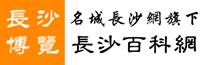幕阜山余脉
岳麓山,又称麓山,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。属南岳衡山之余脉,或曰第七十二峰。南北朝刘宋时《南岳记》载:“南岳周围八百里,回雁为首,岳麓为足。”故名岳麓。岳麓山方圆八平方公里,主峰近三百米。清代诗人薛柱斗有诗云:
立马高山逸兴赊,翘然四望渺无涯。
遥瞻云起烟封处,笑指长沙十万家。
现在,“长沙十万家”已成长沙百万家了。
岳麓山水秀山青,自古有奇、珍、幽、美之称。岳麓山最大的特点是将儒、佛、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,使之成为了无可取代之圣地。儒者,岳麓书院也。岳麓书院创立于宋开宝九年(976)。在这之前,书院已具雏形。史载岳麓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叫周式,此人以行侠仗义著称,据说他主事不到三年,就声名远播,连远在汴京的皇上宋真宗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,想封他为“国子监主簿”,但周式无意于仕途,执意要回岳麓书院。宋真宗还算开明,不但没为难他,还题了“岳麓书院”四字相赠。岳麓书院目前是中国保存完好的古代四大书院之首。其次是岳麓山的半山腰有一麓山寺,又称岳麓寺,系湖南最早的寺院,湖南佛教的发源地,故寺前门联曰:“汉魏最初名胜,湖湘第一道场。”山顶上有云麓宫,始建于明成化十四年,为明代吉简王就藩长沙时倡建,乃道家七十二福地之二十三洞真虚福地。现门额为“云麓道宫”金匾,门旁有联:“对云绝顶犹为麓,求道安心即是宫。”在云麓宫的下方有“飞来石”和“自来钟”两处景点。
民国著名女作家谢冰莹曾在《爱晚亭》一文中说到岳麓山有一个最大的特点,那便是“先烈先贤古迹多,使游人处处受到一种感动和启示。他们一面欣赏名胜,一面缅怀先烈那种为国牺牲的精神,不由得从内心发生一种崇敬和景仰。”登岳麓山有好几条路,如果从清风峡往白鹤泉,直上云麓峰,再往南拐至穿石坡,之后再往北至禹碑峰,再往北至赫石坡,那么,便可依次见到如下的墓及墓庐:辛亥援鄂五护国阵亡将士公墓、刘道一墓、覃理鸣墓、肖伟墓、蒋翊武墓、张辉瓒墓、蔡锷墓、黄兴墓、谭馥墓、陈作新墓、吴道行墓、刘昆涛墓、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公墓、李仲麟墓、黄爱庞人铨合墓、丁文江墓、胡子靖墓、陈天华姚宏业双冢墓、禹之谟墓、彭遂良彭昭合墓、焦达峰墓、高继青墓、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、杨树达墓、林修梅墓等。
岳麓山还有一座著名的爱晚亭。据载:清乾隆五十七年(1792),岳麓书院院长罗典在岳麓书院的后山,清风峡的峡口创建了一座“红叶亭”。后来湖广总督毕沅,根据唐人杜牧的《山行》一诗,将其改名为“爱晚亭”。有一则关于“爱晚亭”名字由来的民间故事,说是袁枚到岳麓书院拜访罗典,罗典因袁枚招收过女弟子而托病不见。袁枚无奈,只好转到后面岳麓山去游玩。刚到清风峡峡口,便见一飞檐古亭迎面而来。红叶,古亭,还有潺潺的溪水如琴,袁枚叫一声好,立马又感到了一种遗憾,那就是古亭上的“红叶亭”三字过于直白。于是,他便要书童拿出纸笔,将唐代杜牧的《山行》诗草出,并有意地将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中的“爱”和“晚”二字遗漏。这一幅字很快就到了院长罗典的手中。罗典一见,便知端详,他知道是袁枚要他将“红叶亭”改为“爱晚亭”。罗典自然知道这一改的妙处,但他不愿把这个面子卖给袁枚,于是,他便给湖广总督毕沅修书一封,请总督大人题上“爱晚亭”三字。这传说是否可信,暂不去管它,但“爱晚亭”三字为毕沅所题,却明确记载在《岳麓书院志》上。
清风峡位于山之东麓。清康熙《岳麓志》载:“清风峡在岳麓寺前,双峰相夹中有平壤,纵横十余丈,紫翠青葱,云烟载日。当溽暑时,清风徐至,人多憩休,故名以此得。”历代名贤多有诗赋吟咏。南宋乾道元年(1165),号称“东南三贤”之一的张栻主持长沙岳麓书院,常来此游憩,作有《清风峡》诗,诗云:
扶疏古木矗危梯,开始至今几摄提。
还有石桥容客座,仰看兰若与云齐。
风生阴壑方鸣籁,日烈尘寰正望霓。
从此上山君努力,瘦藤今日得同携。
谢冰莹对“清风峡”(又作“青枫峡)的感受颇深,她说:“在青风峡里听涛声,比在衡山黑龙潭听瀑布还有趣,微风起时,枫叶便发出轻细的软语,恰像爱人躲在树丛喁喁情话。猛不防,一阵疾风吹来,松涛像万马奔腾,鼓乐齐奏,使你听了好像觉得天地在旋转,万物在歌唱,在狂舞。这时候,你根本忘记了自身的存在,只觉得大自然的伟大,神秘。你到了这样的境界,你完全与大自然合二为一,你没有忧愁,没有烦恼,没有痛苦。你所感到的只是自我的渺小与无能,你恨不能化身为落叶,随风飘荡,该有多么轻松和自由。回头再看看水里的鱼虾和螃蟹,你会更羡慕它们的无拘无束,自由自在。所以我说青枫峡和爱晚亭简直是人乐以忘忧的仙境。”
总而言之,岳麓山是长沙的地标名片,既有出类拔萃的自然之美,又有内涵深厚的人文之美。没到过岳麓山,就等于没到过长沙。这样说,虽有点夸张,但也在情理之中。
撰文:陈先枢
摄影:乔育平
来源:2018年8月《长沙百景》
编辑:周顺